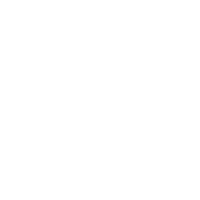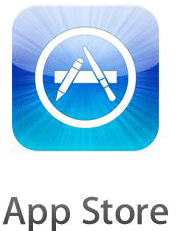第314章

- A-
- A+
餐厅里。
爸妈加餐了,芝宝当然也要加餐。
它坐在专门为它添置的高椅上,戴着吃饭兜兜,斯文地并拢爪子,低着脑袋一点都不斯文地大口干饭,恨不得一口把碗里所有东西都吃完。
另一边。
林浅喝着海鲜咸粥,喝一口说十句话:“我看到你给我发的信息,那意思应该是请我回梨园,我没理解错吧?”
傅聿川沉默。
变相默认。
“这栋别墅我住了三年,屋子里的所有东西都是我置办的,说来也都有感情。既然你邀请我,那我就住下了。”
“跟以前咱们刚结婚那会儿一样,我住主卧,你住书房,同在一个屋檐下互不干扰。我估计要在京城待蛮长一段时间,你不用过多理会我,忙你自己的事就行。”
林浅左手撑了撑下巴,捏着勺子的右手下意识去舀碗里的海鲜粥,喝了两口之后,感觉有什么不对劲。她低头,看向面前的瓷碗,里头满满的虾肉,粥也是被增加过的。她喝了一小半,傅聿川就在她说话的时候给她添满。
她说呢。
怎么一小碗粥喝了大半个小时还没喝完。
这谁能喝得完?
-
深夜。
别墅的照明灯陆续熄灭了。
林浅现在一日三次都在喝抗癌的中药,药物的作用下,她夜里睡得比以前早了。约莫十点半,傅聿川切了一小盘她喜欢吃的新鲜水蜜桃过来,就看见她坐在客厅羊毛绒地毯上,抱着芝宝睡着了。
小猫明显还想玩平板里的抓星星游戏,但看见她睡了,也便不闹不吵地趴在她怀里,任由她将它当成软绵绵的抱枕。
她说想养一只猫。
取名芝宝。
傅聿川便在一年前买了这只橘白色的猫咪,叫这个名字。经常给它看她的照片,让它能在看见她的第一眼就亲近她讨她喜欢。原本是打算今年等她身体好些了,就请南老将猫咪送给她,不曾想她会回京城。
傅聿川放下手里的水果,走到她身旁,将亮着屏的平板收好,喊了芝宝一声让它去猫窝睡觉,橘猫软声喵了喵,听话地往小窝去了。他弯腰,把睡着的林浅从地毯上捞了起来,径直走向二楼主卧。
将她稳妥放在大床上。
盖好被子。
又点了她平日里喜欢的安眠熏香。
做完这一切,傅聿川并没有离开,而是站在床边,借着床头昏黄的睡眠灯光,安静地凝着她姣好的睡颜。
9月30号她盛装出席在南老的寿宴上,他们在半壁江山台阶处相遇。她以旧友的目光笑着与齐特助交谈,以嫂子的身份宠溺地夸傅寒很棒,唯独对着他,她客气又疏离,一句傅总将两人的关系划分成楚河汉界。
那一刻他疼了。
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尖锐疼痛感,从皮肤渗入骨血,蔓延全身每个细胞。就好像心口被塞了一块积了水的棉花,沉甸甸的。
她在宴会厅里那些小动作,待在他身旁的局促、不自然、不适应等等,所有细枝末节落入他视线里,都像无形的银针,扎得人泛疼。
他从出生开始就被人追杀,每天过的都是担惊受怕的日子。母亲去世后,7岁的他独自在伦敦求生,一路走到现在早就麻木了,不知道疼也不清楚什么是苦。
爸妈加餐了,芝宝当然也要加餐。
它坐在专门为它添置的高椅上,戴着吃饭兜兜,斯文地并拢爪子,低着脑袋一点都不斯文地大口干饭,恨不得一口把碗里所有东西都吃完。
另一边。
林浅喝着海鲜咸粥,喝一口说十句话:“我看到你给我发的信息,那意思应该是请我回梨园,我没理解错吧?”
傅聿川沉默。
变相默认。
“这栋别墅我住了三年,屋子里的所有东西都是我置办的,说来也都有感情。既然你邀请我,那我就住下了。”
“跟以前咱们刚结婚那会儿一样,我住主卧,你住书房,同在一个屋檐下互不干扰。我估计要在京城待蛮长一段时间,你不用过多理会我,忙你自己的事就行。”
林浅左手撑了撑下巴,捏着勺子的右手下意识去舀碗里的海鲜粥,喝了两口之后,感觉有什么不对劲。她低头,看向面前的瓷碗,里头满满的虾肉,粥也是被增加过的。她喝了一小半,傅聿川就在她说话的时候给她添满。
她说呢。
怎么一小碗粥喝了大半个小时还没喝完。
这谁能喝得完?
-
深夜。
别墅的照明灯陆续熄灭了。
林浅现在一日三次都在喝抗癌的中药,药物的作用下,她夜里睡得比以前早了。约莫十点半,傅聿川切了一小盘她喜欢吃的新鲜水蜜桃过来,就看见她坐在客厅羊毛绒地毯上,抱着芝宝睡着了。
小猫明显还想玩平板里的抓星星游戏,但看见她睡了,也便不闹不吵地趴在她怀里,任由她将它当成软绵绵的抱枕。
她说想养一只猫。
取名芝宝。
傅聿川便在一年前买了这只橘白色的猫咪,叫这个名字。经常给它看她的照片,让它能在看见她的第一眼就亲近她讨她喜欢。原本是打算今年等她身体好些了,就请南老将猫咪送给她,不曾想她会回京城。
傅聿川放下手里的水果,走到她身旁,将亮着屏的平板收好,喊了芝宝一声让它去猫窝睡觉,橘猫软声喵了喵,听话地往小窝去了。他弯腰,把睡着的林浅从地毯上捞了起来,径直走向二楼主卧。
将她稳妥放在大床上。
盖好被子。
又点了她平日里喜欢的安眠熏香。
做完这一切,傅聿川并没有离开,而是站在床边,借着床头昏黄的睡眠灯光,安静地凝着她姣好的睡颜。
9月30号她盛装出席在南老的寿宴上,他们在半壁江山台阶处相遇。她以旧友的目光笑着与齐特助交谈,以嫂子的身份宠溺地夸傅寒很棒,唯独对着他,她客气又疏离,一句傅总将两人的关系划分成楚河汉界。
那一刻他疼了。
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尖锐疼痛感,从皮肤渗入骨血,蔓延全身每个细胞。就好像心口被塞了一块积了水的棉花,沉甸甸的。
她在宴会厅里那些小动作,待在他身旁的局促、不自然、不适应等等,所有细枝末节落入他视线里,都像无形的银针,扎得人泛疼。
他从出生开始就被人追杀,每天过的都是担惊受怕的日子。母亲去世后,7岁的他独自在伦敦求生,一路走到现在早就麻木了,不知道疼也不清楚什么是苦。
 我要评论
我要评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