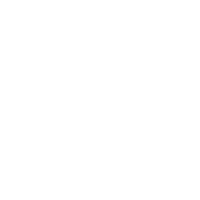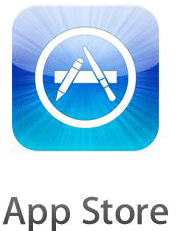第85章

- A-
- A+
希望换宿舍的事儿早点提上议程才好 。
程遥遥洗了头和澡,穿着一条睡裙,在箱子里翻找东西,拿出一个精致的小钱袋。打开一看,呵,原主的财产可真不少!
厚厚的一叠票。花花绿绿,程遥遥盘腿坐在床上清点起来。全国粮票,工业票,皮鞋票,布票,糖票,点心票,肥皂票,还有……月经带票。
其实程遥遥从原主的记忆里继承了关于票据的知识,只是拿着这一叠票,程遥遥还是为这个年代票据之精细感到震惊。
原主从没受过穷,她父亲一个月工资有百来块,有一大半都花在大女儿身上了。程遥遥今天穿的那件粉色小洋装罩衫,就是原主父亲花了两个月工资从广州给她带回来的。可惜,在三年前,原主父亲的天平就渐渐往程诺诺身上倾斜了。
虽然还不至于偏心程诺诺,对原主无条件的宠溺也渐渐收起,变成了雨露均沾。原主下乡时,父亲给原主和程诺诺的钱是一样的,一人一百块,不过额外给原主补贴了五十斤全国粮票。这些还是他瞒着程诺诺母亲偷偷攒下的。
程遥遥清点了一下票据,可惜全国粮票和点心票糖票都只剩一点,余下的都是工业票这些用不上的。钱也只剩了三十七块八毛。
一百块钱啊,甜水村一大家子,一年到头也赚不下这么多公分。一百块够他们用一年了!原主三个月就花得差不多了:在黑市上买点心,买零嘴,买新衣服,回回进城都要下馆子。还顺带养活了一个刘敏霞。
程遥遥也不觉得多震惊,她自己上辈子更能花钱,蓝血品牌vip客户,各种全球限量的包和鞋,一上新就成批送到家里的。
现在她却盘腿坐在这儿,一分一毛地数钱。
原始森林里大雨瓢泼, 谢三冒雨追赶一只野猪进了深山,四周昏昧晦暗,只听得见他自己的心跳和喘息。身后草丛忽然传出窸窣动静, 谢三警惕地握住柴刀, 猛然转身。
却是淋得一身湿漉漉的程遥遥。她穿着初见时那件粉色衣裳,赤着雪白的一双足, 站在那儿冲他叫:“谢三哥……”
程遥遥黑发雪肤, 眼下一颗泪痣点缀万千风情, 玫瑰色的唇润着水光,美得摄人心魄,像林中的精怪。
谢三不由得后退一步。程遥遥见他不理, 忽然又叫:“我脚好痛!”
这一声带着哭腔,奶声奶气,准确无误地挠在人心口最痒处。低头看去,那雪白足弓上两点鲜红, 是蛇咬出的伤口。
谢三着魔似的伸出手,不知为何, 程遥遥便一下子跌进了他怀里。她比一朵花还轻还软,散发着甜甜的玫瑰香。
……
“……”谢三猛然睁眼, 瞪着黑漆漆天花板大口大口喘着气,浑身汗淋淋如同刚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, 身下草席都浸湿了。
他撑着床坐起来,忽然感觉到裤子里一阵凉凉的,登时浑身僵硬, 半晌,给了自己一巴掌。
他已经二十岁,身体强壮,这样情况时常发生,可那梦是朦朦胧胧没有形象的,没有哪一次是这般香艳旖旎……她是天上的云,便是想一想也是亵渎,何况……
程遥遥洗了头和澡,穿着一条睡裙,在箱子里翻找东西,拿出一个精致的小钱袋。打开一看,呵,原主的财产可真不少!
厚厚的一叠票。花花绿绿,程遥遥盘腿坐在床上清点起来。全国粮票,工业票,皮鞋票,布票,糖票,点心票,肥皂票,还有……月经带票。
其实程遥遥从原主的记忆里继承了关于票据的知识,只是拿着这一叠票,程遥遥还是为这个年代票据之精细感到震惊。
原主从没受过穷,她父亲一个月工资有百来块,有一大半都花在大女儿身上了。程遥遥今天穿的那件粉色小洋装罩衫,就是原主父亲花了两个月工资从广州给她带回来的。可惜,在三年前,原主父亲的天平就渐渐往程诺诺身上倾斜了。
虽然还不至于偏心程诺诺,对原主无条件的宠溺也渐渐收起,变成了雨露均沾。原主下乡时,父亲给原主和程诺诺的钱是一样的,一人一百块,不过额外给原主补贴了五十斤全国粮票。这些还是他瞒着程诺诺母亲偷偷攒下的。
程遥遥清点了一下票据,可惜全国粮票和点心票糖票都只剩一点,余下的都是工业票这些用不上的。钱也只剩了三十七块八毛。
一百块钱啊,甜水村一大家子,一年到头也赚不下这么多公分。一百块够他们用一年了!原主三个月就花得差不多了:在黑市上买点心,买零嘴,买新衣服,回回进城都要下馆子。还顺带养活了一个刘敏霞。
程遥遥也不觉得多震惊,她自己上辈子更能花钱,蓝血品牌vip客户,各种全球限量的包和鞋,一上新就成批送到家里的。
现在她却盘腿坐在这儿,一分一毛地数钱。
原始森林里大雨瓢泼, 谢三冒雨追赶一只野猪进了深山,四周昏昧晦暗,只听得见他自己的心跳和喘息。身后草丛忽然传出窸窣动静, 谢三警惕地握住柴刀, 猛然转身。
却是淋得一身湿漉漉的程遥遥。她穿着初见时那件粉色衣裳,赤着雪白的一双足, 站在那儿冲他叫:“谢三哥……”
程遥遥黑发雪肤, 眼下一颗泪痣点缀万千风情, 玫瑰色的唇润着水光,美得摄人心魄,像林中的精怪。
谢三不由得后退一步。程遥遥见他不理, 忽然又叫:“我脚好痛!”
这一声带着哭腔,奶声奶气,准确无误地挠在人心口最痒处。低头看去,那雪白足弓上两点鲜红, 是蛇咬出的伤口。
谢三着魔似的伸出手,不知为何, 程遥遥便一下子跌进了他怀里。她比一朵花还轻还软,散发着甜甜的玫瑰香。
……
“……”谢三猛然睁眼, 瞪着黑漆漆天花板大口大口喘着气,浑身汗淋淋如同刚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, 身下草席都浸湿了。
他撑着床坐起来,忽然感觉到裤子里一阵凉凉的,登时浑身僵硬, 半晌,给了自己一巴掌。
他已经二十岁,身体强壮,这样情况时常发生,可那梦是朦朦胧胧没有形象的,没有哪一次是这般香艳旖旎……她是天上的云,便是想一想也是亵渎,何况……
 我要评论
我要评论